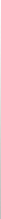范蠡(約公元前518年~前445年)��,字少伯,春秋末期楚國宛邑(今河南南陽)人����,生于宛郡的內(nèi)鄉(xiāng)縣,出身貧苦�,但素有大志,見識高卓�。范蠡在青年時就已經(jīng)學(xué)富五車、滿腹經(jīng)綸����,而且聰敏睿智、胸藏韜略���,頗有圣人之資�,再加上他精通劍法,可以說是文武雙全��。然而�,他卻懷才不遇,只好每日修身養(yǎng)性�,過著“茍全性命于亂世,不求聞達(dá)于諸侯”的隱居生活�����。終于有一天�,楚國宛令文種到各地訪求名士,才發(fā)現(xiàn)范蠡這匹“千里馬”��。兩人交談之后�����,一同棄楚國而去����,投奔了越國。公元前496年����,越王允常駕崩��,其子勾踐即位����。吳王闔閭聽說了允常的死訊之后���,便趁越國人心不穩(wěn)之際興師伐越���,交戰(zhàn)于樵李(今浙江嘉興)。兩軍對陣��,勾踐用死囚做死士��,在吳軍面前叫陣�,然后這些人就在吳軍陣前自殺�����。吳國軍士見狀����,大驚失色��,人心浮動��。勾踐率領(lǐng)越軍趁機(jī)發(fā)起攻擊����,原本強(qiáng)大的吳軍瞬間潰散��,一敗涂地�。吳王闔閭在混戰(zhàn)中也身負(fù)重傷,只好退兵�����,返回姑蘇城內(nèi)�。沒過多少時日,吳王闔閭的傷病惡化�,生命岌岌可危。臨終前�,吳王闔閭把其子夫差叫到床前,叮囑他一定不要忘記與越國的仇恨�。夫差即位后,日夜操練軍隊��,秣馬厲兵���,準(zhǔn)備消滅越國���。勾踐見狀����,決定先發(fā)制人����。范蠡和文種認(rèn)為時機(jī)不利于越國,極力勸阻�,但勾踐求勝心切,根本聽不進(jìn)任何不利之言�,于公元前494年率兵進(jìn)攻吳軍守地——夫椒(今浙江紹興),吳越大戰(zhàn)就這樣開始了���。夫椒一戰(zhàn)���,越軍大敗����,勾踐的軍隊只剩下了殘兵敗將五千余人,無奈之下����,只好退守會稽山�。會稽山雖然地勢險要�,易守難攻,但夫差率軍只圍不攻���,不久�����,缺水少糧的越軍支持不住了��,傷殘兵士的哀號遍布山野�。見此情形�����,勾踐欲拔劍自刎���,吳王闔閭再次竭力勸阻����,并設(shè)法用重金賄賂了吳王夫差身邊的寵臣����,才得以保全勾踐的性命�。從此��,文種回國主持政事���,范蠡則隨勾踐及妻室來到吳國�����,住進(jìn)石屋�,開始了忍辱負(fù)重的人質(zhì)生涯�����。勾踐在吳國寄人籬下����,受盡了吳王夫差的嘲諷和欺凌。但范蠡足智多謀�����,終于使勾踐取得了吳王夫差對他的信任��。范蠡對夫差說���,當(dāng)初勾踐只是心浮氣盛���,所以才膽敢進(jìn)攻夫椒,但如今他對吳王的謀略心服口服�,愿意回國對吳王每年納貢稱臣。現(xiàn)在越國無人治理�,一片混亂,連年饑荒�,倒不如放勾踐回國,每年可以進(jìn)貢更多的財物�。在范蠡的努力之下,勾踐在作了3年人質(zhì)后返回越國�。歸國后,范蠡向勾踐提出了一整套休養(yǎng)生息的政治主張�,他說:“廣天下,尊萬乘之主�����;使百姓安其居�,樂其業(yè)者,惟兵。兵之要在于人���,人之要在于谷�����。谷多��,則兵強(qiáng)����。王而備此二者�����,然后可以圖之也�。”這一主張得到了勾踐的贊同��。在范蠡與文種的鼎力輔佐下����,勾踐大赦天下,減收稅賦�����,使人民得以還田勤耕,充實了國庫和糧倉�����。隨著生活的日益殷實����,越國人丁日趨興旺����,皆具“帶甲之勇”,國力迅速恢復(fù)和發(fā)展����,一躍成為東方強(qiáng)國。在公元前473年�����,勾踐終于滅掉了宿敵吳國��,報了會稽之恥���。接著��,范蠡又協(xié)同勾踐北渡淮河����,在徐州大會齊、晉等諸文種侯����,使周元王不得不封勾踐為伯,號令中原��,被諸侯稱為“霸王”��。在范蠡的輔佐下���,勾踐成為春秋時期的最后一位霸主�����。此時�����,勾踐欲封范蠡為上將軍��,把越國分一部分給他作為酬謝��,但范蠡深知“狡兔死���,走狗烹���;飛鳥盡�,良弓藏”的道理,沒有接受越王的封賞���,并執(zhí)意棄官從商����。據(jù)說���,范蠡從商之后����,曾經(jīng)更換過三個地方�����,但是他無論從事什么行業(yè),都是天下名流��,名垂后世��。特別是在陶邑(今山東定陶)的時候���,其資產(chǎn)由“十萬”到“千金”�����,再至“巨萬”�,成為當(dāng)時排名第一的富賈��。由于當(dāng)時范蠡自稱為“朱公”�,因此在民間也就有了“陶朱公”之稱。